

戴望舒常以“雨巷诗人”的朦胧形象留驻文学史,但深入历史烟云,他更是一位以笔为剑、以身殉国的文化战士。
在民族危亡之际,他走出悠长寂寥的雨巷,踏入血火交织的战场,其政治轨迹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从苦闷彷徨到投身救国的精神蜕变。

一九二六年
凝泪出门
昏昏的灯,溟溟的雨,
沉沉的未晓天;
凄凉的情绪;将我底愁怀占住。
凄绝的寂静中,你还酣睡未醒;
我无奈踯躅徘徊,独自凝泪出门:
啊,我已够伤心。
清冷的街灯,照着车儿前进:
在我底胸怀里,
我是失去了欢欣,愁苦已来临。
一、 革命熔炉的淬炼
上海大学的红色启蒙
1923年,18岁的戴望舒考入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。这所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的“红色学府”成为他政治觉醒的起点。
在这里,他不仅师从茅盾、田汉等文学大家,更主动跨系聆听瞿秋白的社会学课程,初探马克思主义理论。
课堂上,田汉介绍的法国象征派诗歌滋养了他的艺术灵魂;而瞿秋白剖析的社会矛盾,则点燃了他的革命理想。
五四运动的狂潮中,上海大学成为风暴中心。戴望舒与同学投身反帝示威,亲身经历了租界军警的镇压和学校的查封。这段经历使他深刻认识到文学与政治的不可分割。
1926年,他在震旦大学加入共青团,次年更“跨党”加入国民党——这种双重身份映射出大革命年代进步青年的复杂选择。
当“四一二”政变的枪声击碎革命幻想,他避难松江,在《雨巷》的忧郁吟哦中,既流露着白色恐怖下的迷惘,也暗藏对“丁香般希望”的执着等待。
二、香江战旗
《星座》副刊与抗日铁骨
抗战烽火重塑了戴望舒的文学与政治生命。1938年,他南渡香港主持《星岛日报》副刊《星座》,将这片文化阵地转化为抗日号角。
在创刊词中,他誓言以文字为星光,“代替天上的星星,与港岸周遭的灯光尽一点照明之责”。他汇聚郭沫若、茅盾、艾青等左翼作家,使《星座》成为抗战文艺的重要堡垒。
面对港英当局的审查,戴望舒以“开天窗”、加注“此处删去百余字”等策略进行无声抗议。
1941年香港沦陷,日军因《星座》的抗日立场将他逮捕。在潮湿阴暗的牢房里,他遭受酷刑却坚贞不屈,更以鲜血写下铁骨铮铮的诗篇:
一九四二年
狱中题壁
如果我死在这里,
朋友啊,不要悲伤,
我会永远地生存
在你们的心上。
你们之中的一个死了,
在日本占领地的牢里,
他怀着的深深仇恨,
你们应该永远地记忆。
一九四二年
我用残损的手掌
我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
贴在上面,寄与爱和一切希望,
因为只有那里是太阳,是春,
将驱逐阴暗,带来苏生,
因为只有那里我们不像牲口一样活,
蝼蚁一样死⋯⋯
那里,永恒的中国!
以意象化的手法抚摸“血和灰”中的祖国山河,最终将全部希望寄托于那“遥远的一角”——延安抗日根据地,那里有“太阳”和“春”。
这些诗作彻底褪去了早期《雨巷》的朦胧哀愁,迸发出战斗的火焰与信念的光芒,成为抗战诗歌的不朽丰碑。
三、光明前夕
政治清白的捍卫与未竟的理想
抗战胜利后,戴望舒的政治立场愈发鲜明。
1946年,任教暨南大学期间,他因支持学生民主运动遭解聘。
1948年,国民党当局污蔑他为“香港汉奸文人”,发出通缉令。为证清白,他毅然宣告:“我不想再留在香港了,我必须去北方。就算死,我也要死得有尊严。”
1949年3月,他辗转抵达北平,以满腔热忱投身新中国文化建设。
在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任职期间,他承担起毛泽东《论人民民主专政》法译本的审定工作。
令人扼腕的是,1950年2月,多年哮喘与狱中伤病夺去了他45岁的生命。
弥留之际,他递交了入党申请书——这位历经沧桑的诗人,最终以对共产主义信仰的追随,为自己波澜壮阔的政治生涯写下句点。
一九二七年
雨巷
撑着油纸伞,独自
彷徨在悠长,悠长
又寂寥的雨巷,
我希望飘过
一个丁香一样地
结着愁怨的姑娘。
戴望舒的政治轨迹,映照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在时代巨变中的精神长征。他从象征主义的“雨巷”走向民族解放的“烽火星座”,其政治选择始终以民族大义为轴心。
早年上海大学的红色启蒙、抗战香港的文化抵抗、以及最终对新中国的赤诚奔赴,构成了一条清晰而坚定的思想脉络。
在诗与政治的交织中,他以生命践行了“用残损的手掌”托举民族未来的誓言——这不仅是一位诗人的政治抉择,更是一个民族在血火中寻求重生的精神象征。
(以上图文内容来源于网络,侵权即删)
更多内容可查阅馆藏资源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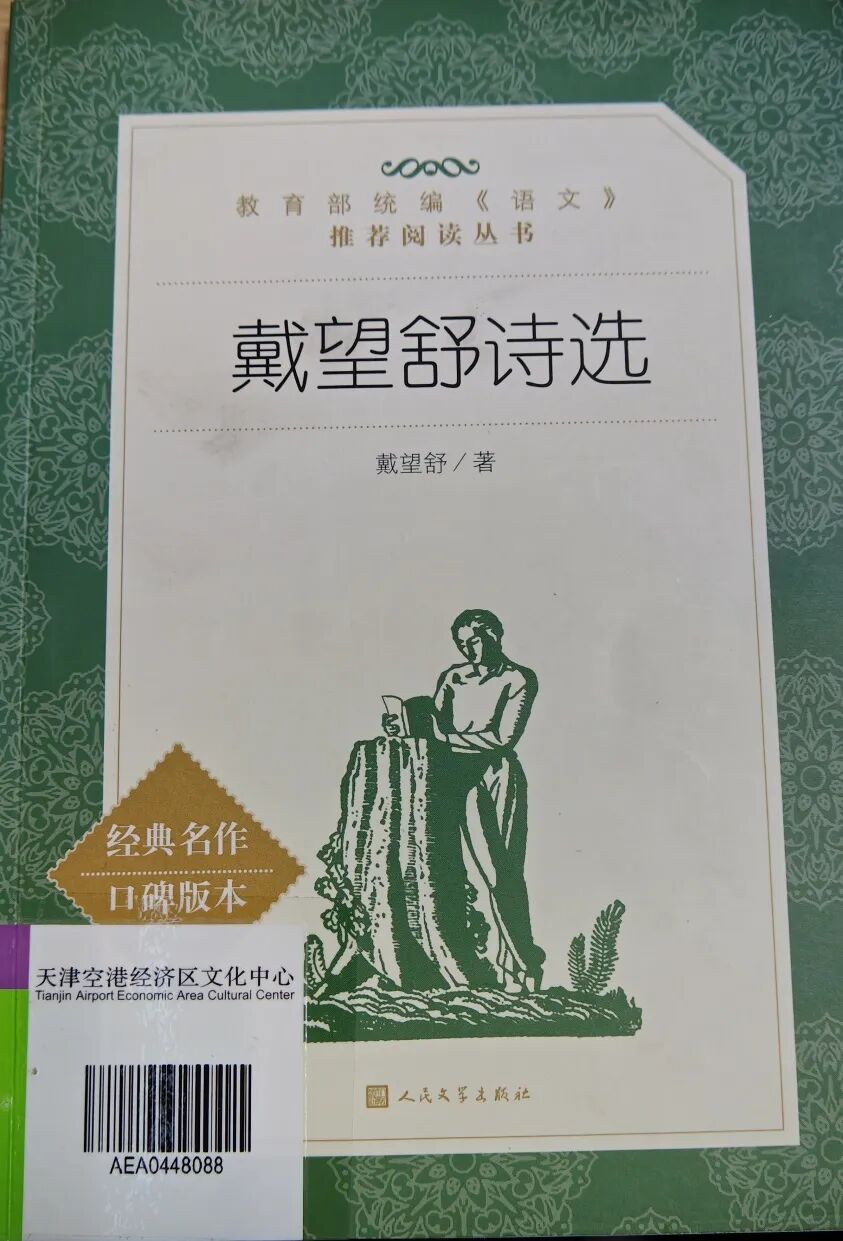
《戴望舒诗选》
馆藏地点:2楼青少年阅读中心03排04列3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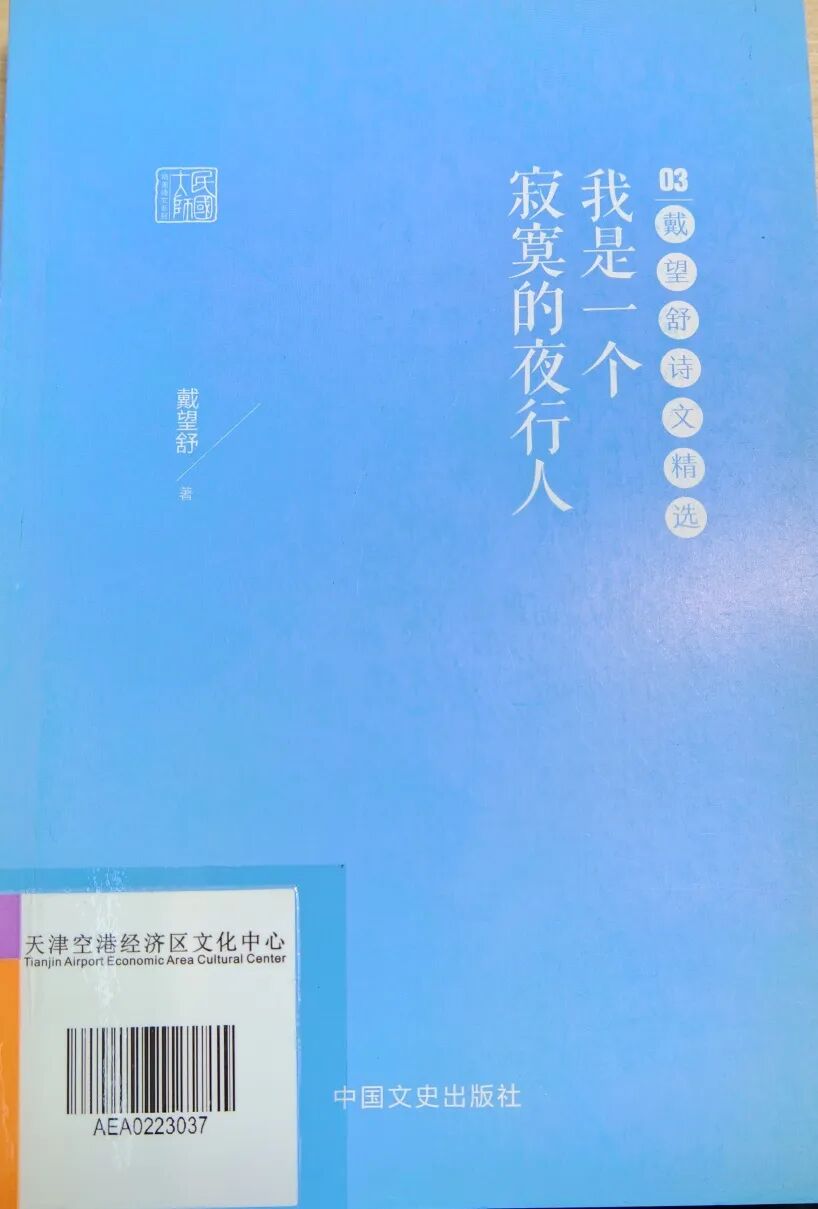
《我是一个寂寞的夜行人:戴望舒诗文精选》
馆藏地点:2楼第一图书借阅室39排02列4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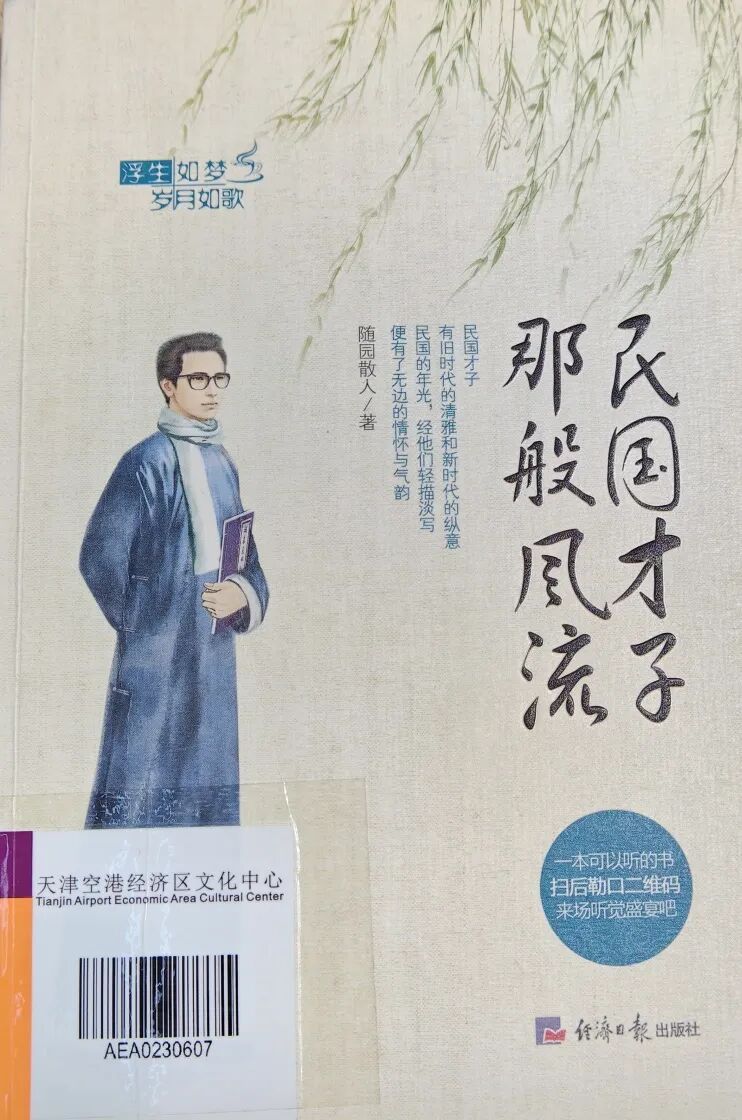
《民国才子那般风流》
馆藏地点:3楼第二图书借阅室15排11列4层
文案提供:第一图书借阅室